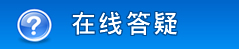党组书记、检察长:屈新
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和要求。抓紧制定一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一、制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进步意义
(一)防止权力被滥用,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把影响力看成是可能造成腐败的能力和能量,实际上是在对权力进行更全面的约束,相当于一个提醒和规范。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定,不仅能有效阻击腐败期权化的现象,让那些期待权力若干年后变现的官员改变自己的想法;还能够净化社会上流行的凡事找关系找人的腐败风气,让规则的运行更加清晰而公正。这对于防止权力的影响力被滥用,有效地预防腐败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搭建了以法治腐的构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确立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其对我国以法治腐之路的影响。对于惩治腐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方法去发现、揭露,通过法律裁判为有罪并判处刑罚无疑是最有效的、最终极的途径。纵观我国贪污贿赂罪的确立历程,从明确的罪名来看,基本经历了主体上从现职的国家公职人员到离退休人员、近亲属及关系人等非国家公职人员,行为上从直接利用公职人员本人的职权到间接利用职权(介绍贿赂)再到利用影响力的过程。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立,使受贿在主体和行为上均完成了逻辑上的完整,因此至少可以说,在法制层面,以法治腐的架构已经搭建起来了。
(三)弥补了法律漏洞
我国刑法打击受贿罪,以前仅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现在打击受贿罪的范围扩大,更让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表现在:一方面新司法解释从法律角度对官员约束亲友行为提出了更高的廉政要求,有利于消除官员曲线受贿、捞钱的侥幸心理,扎紧了反腐制度篱笆。另一方面,新司法解释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列入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范围,也是一大亮点。在现实生活中,离职官员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情况并不少见。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他罪的界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刚刚确立的新罪名,其与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何进行界定,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关系
第一,仅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不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第二,仅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1)如果近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人单方收受了贿赂,但未将此情况告知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是一味要求被利用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该国家工作人员对此也不知情,则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近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人收受贿赂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为徇私情而违背职务构成犯罪的,则按相应的犯罪论处。若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这是他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受贿,也未直接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但却对该情况的存在予以默许或者默认,而他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但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起到了暗中配合帮助的作用,那么他人构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考虑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片面共犯; (2)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行为人没有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亲友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本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不是斡旋受贿犯罪。
第三,仅构成受贿罪。国家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等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领导干部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本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领导秘书等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斡旋受贿犯罪,应按受贿罪定罪处罚。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界限
介绍贿赂罪的主体是在请托人和受贿人之间穿针引线,创造条件让双方互相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作中间联络,甚至传递贿赂物品,起媒介作用,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的交易。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行为主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而国家工作人员本身并未参与该行为。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若自然人冒充、自吹系某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是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而收受、索取了他人的财物,这显然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宜以诈骗罪对其定罪量刑。
(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必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只有请托人得到的是不正当利益,对行为人才可以本罪追究。如果请托人获取的利益是法律、法规允许的,是正当的利益,这个利用影响力交易的人,无论收到多少钱,无论在多少个国家工作人员中穿针引线,都不构成犯罪。其索取或收受财物应为违法所得,应该收缴或返还被索贿人。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台,将会有力遏制那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的受贿行为逍遥法外,使反贿赂罪的法网不再有重要遗漏,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打击贿赂犯罪。但是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犯罪主体应进一步扩展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的确立,在理论上是对传统受贿罪的一次重大突破,在实践中也填补了目前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一个空缺。其犯罪主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外,还包括“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因此,犯罪主体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依法扩展。但是,当今我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行为,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杂七杂八的专门替别人跑关系的“公关公司”,多是收取当事人的钱财,替当事人谋取利益的“特别公司”。这些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往往并不是关系密切的人,如果“公关公司”收取当事人钱财后,再通过非财产性贿赂等手段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公关公司”就不构成任何犯罪。这些专门拉国家工作人员下水的“公关公司”,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相当大的,而新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他们缺乏应有的打击。因此,为有利打击腐败行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还应进一步扩展,不应仅包括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且应把所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进行受贿的人或单位都包含在内,只有这样才能不使那些违法之徒钻法律的空子。
(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制约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按照现有的司法解释,“不正当利益”指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益本身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即利益本身不正当;二是提供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帮助或方便条件,也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手段不正当,也可能利益本身是正当的。但是,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利益本身是正当时,无论通过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因此,实践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为了谋取某种正当利益,特别是这种利益非常重大时,常常会花费钱财,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打招呼、疏通关系,要求仅仅是“依法给予办理”或“依法尽快给予办理”。那么,接受当事人钱财从中疏通关系的人,无论收受或索取多少钱财,只要其行为未触犯刑法其他罪名,就不会构成任何犯罪,因为其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这种规定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人谋取不义之财留下不应有的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更有效地遏制腐败,应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方面进行制约,谨防滥用自由裁量权。
(三)举证方面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经出台,有些学者就担心这会成为贪官的“免罪符”,其实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索贿受贿的,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对此不知情,行为人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如果他知情,并相互“通谋”,应视为共同犯罪,那么罪名就是受贿罪。但是在实践中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如一个案件有请托人、有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人,国家工作人员最后也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并拿了钱,但他可能不承认拿钱及存在共谋,证据比较软,但密切关系人拿钱是确定的。这时司法机关就可能把国家工作人员抛开不查,只查中间人,最后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这极有可能使受贿罪的共犯减少,使受贿罪的成立范围减少,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范围扩大,从而放纵一些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如果在举证方面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就会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因为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与行为人不存在通谋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为人存在通谋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此知情。那么,此时国家机关工作人与行为人都定受贿罪,他们之间是共同犯罪。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对此不知情或不存在通谋,那么此时,仅对行为人单独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够成犯罪。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而自己却相安无事的情形;而且还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由于证据较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不问不查,或在查处过程中一遇到困难就退而求其次,简单地将罪责归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了事的情形。
- 上一篇:全市驻所监察室工作在义马市召开
- 下一篇:全市监所检察工作座谈会在义马市院召开
 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股票信息
股票信息 火车时刻
火车时刻 万年历
万年历 常用电话
常用电话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航班信息
航班信息 网上地图
网上地图